
最接地气的学科,失去了“感受性”


独家抢先看
人们对社会学也有着不同于其他学科的期待,认为它是“最接地气”的学科,是接近生活的。社会学是一门经验性学科,本文探讨的是社会学和“感受性”。
上个月,“建议专家不要建议”上了热搜。有的专家建议租房不如买房,有的专家建议不要掏空六个人的钱包凑首付,而这些建议很快引起网民反感,结果反被“建议”了。而这段时间,也有人口学专家建议年轻人如果短期内找不到工作,“去结婚生子也行”。他们的话一出,当即被网友吐槽。
也正是因为这些风波,我们产生了一个困惑:与人、社会与经济等现实话题紧密相关的社科专家,为何无法与年轻人共情,为何不能理解他们的处境、情绪。这其中的缘由是多方面的,也是复杂的,能解读的角度也不止一种。我们打算从学科的角度聊一聊这个现象。
此前,我们首先谈了经济学,《“建议专家不要建议”:一个热搜与一门学科》。今天谈的是社会学。社会学是一门经验性学科,除了社会理论、社会学史研究等少数领域,社会学的知识基本上都产生自实证研究。学科角度难免会被理解成对当事人的辩护,“既然是学科问题,又不是某个人的问题”。但有一个悖论是无法忽视的,那就是他们一边做着学问,一边行事与学科气质矛盾。为人治学的这两个方面是如何自洽的?
下面,我们从社会学的“感受”开始说起。
换身衣服,去感受

吴景超(1901-1968),著有《都市社会学》《社会的生物基础》《第四种国家的出路》等。
1925年12月,24岁的中国学生吴景超在美国读书期间去了当年度的“美国社会学年会”听学术报告,几场下来,发现年会上“一大半是本人亲身在都市中调查及研究的结果”,其研究材料全都来自他们在实地的感受、观察,以及与人的交流。
不久后,吴景超连用三组排比句回忆了其见闻:“他们到都市的旅馆里去,到跳舞场中去,到贫民的陋巷中去,到富家的大厦中去搜集材料;他们到工厂中去寻,到裁判所的文件中去寻,到移民到通信中去寻,寻他们所要的材料;他们写信去问,他们亲自跑到人家中去问,他们发出问题单去问,问他们所要知道的事实。”(见商务印书馆《都市意识与国家前途》,2020年8月)当然,社会学研究在当年美国是否达到了如此高的实证化程度,是得打个问号的。吴景超之所以在年会上能见到这个景象,是他本人的兴趣使然。他关心都市、工业和工业化等选题,理所必然,吸引他重点听的是与都市研究相关的报告,而彼时,芝加哥城市学派正处于兴起和扩展的鼎盛年代。该学派以都市实地调查闻名,其主要人物罗伯特·E.帕克(Robert Ezra Park)在1925年当选为年会主办方“美国社会学会”的会长。而以上这些,都是吴景超在现场见到的。在此意义上,他能听到如此之多的都市实地调查也就不足为奇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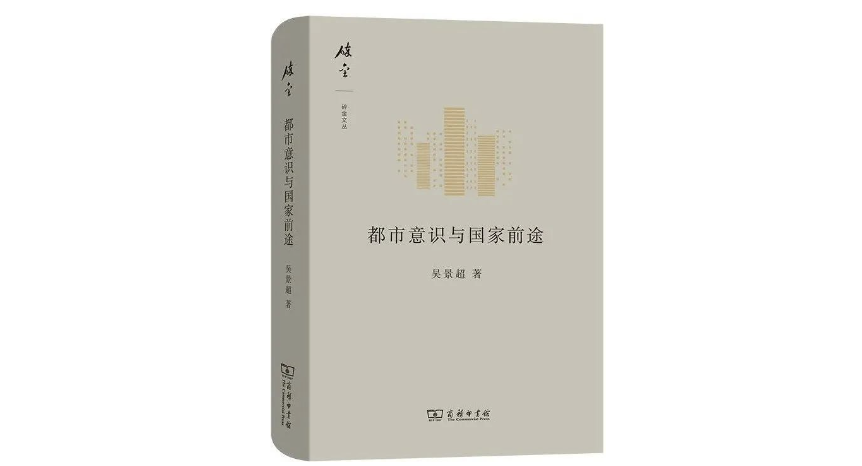
《都市意识与国家前途》,吴景超著,商务印书馆,2020年8月。
在今天的汉语学术界,我们随手翻一本社会科学类的学术刊物便可佐证,吴景超曾经记录的几种实地调查方法早已无处不在,有一些还加入了计量工具,还有一些经历了本土化改造。而简单的社会调查方法在那个年代却是足以让吴景超感到震撼的。
按照他本人的归纳,这是因为当初的中国学者普遍以为读书就是做学问,古人把一生的聪明才力耗尽在几本古书上面,回国的留学生照样只读几本书,只不过换成了外国的古书而已。钱锺书写的《围城》,其背景虽比这晚些时候,对归国学者做学问其实也不乏同等嘲讽。屈指可数的几位社会调查研究者如晏阳初、李景汉和陶孟和等,为人熟知的也只是他们的“乡村建设运动”。整体上,学者们并无意识也并无意愿换身衣服,走出书房。这与19世纪社会学奠基人孔德(Auguste Comte)批判的情形是高度相似的,所以这位早期实证主义者费尽口舌奉劝学者,与其执迷于解读书本知识,不如打开门窗,到外面的世界走一走,去搜集可感受的、可观察的经验性材料。凡基于不可感受的、不可观察的推论都被打入“主观臆断”之列。当然他可能怎么也预料不到,实证研究在随后一个多世纪“一统天下”的扩张速度和规模。这是后话了。

电视剧改编版《围城》(1990)剧照。
其实,生活在新旧文化交替年代的吴景超及其同龄人,不会没有注意到,他们投身于实地社会调查的想法和举动改变了中国知识人的治学方式。尤其是,他们深知虽然早在1904年科举制被废除以后,儒家经典已经退出“经”的位置,“学而优则仕”失去根基,但是另一个传统“坐而论道”还未就此消失。若说“学而优则仕”的退场源于制度变革,那么,“坐而论道”的离场还得取决于发端于他们这一代人的知识变革。唯有他们暂时关上旧书,带着某个理论框架——或空手——去感受真实的中国社会与个体,并以观察、访谈甚至参与式观察等方式获取第一手的经验材料,加以甄别和分析,才有可能产生和积累新知识。
然而,接着要说的是,在社会调查兴起之初,他们未必会重视这样一个问题:“坐而论道”的传统身份(如士绅)是退去了,他们的研究者身份实际上也随之崛起,承接了知识人的某种文化特权传统。
当一个社会学家进入生活世界,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的二元关系就会自动浮现出来。这是不以他们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1929年,晏阳初在做定县调查时曾经真挚地说过,“抛下东洋眼镜、西洋眼镜、都市眼镜,换上一副农夫眼镜”,穿上粗布大褂,希冀以此打破界限。遗憾的是,他们与当地村民“融为一体”的愿望(“欲化农民,须先农民化”)终究在不同时间点落空。当地村民被动进入由研究者创造的二元关系中,成为被研究者,甚至成为被改造者,他们未必了解什么是社会学研究、社会调查,也不知我们这个社会上出现了这样一个工种,就如20世纪90年代一种流行的反思所说的,他们经常把研究者当作“领导派来的”,并因此给予配合,根据研究者设置的议题回答问题。这是今天外出做调查屡屡碰壁、连番被拒的人未曾经历过的。这也说明,研究者被不同程度地祛魅了。
祛魅这个过程也绝不是所向披靡的,而祛魅不了的部分才是研究者普遍具备的一种文化特权。过去的士绅作为知识权威可以教化人、评判人、裁决民事纠纷,研究者则能以“社会调查人员”“课题研究者”“某大学教授”的身份前往一个地方,一个社区,进入他人的生活世界,去感受、去观察、去提问,甚至长期在此生活。更重要的是,研究者来去自如,随时可以退出调查现场,终止感受,借用加缪(Albert Camus)的书名,研究者是走出当地某种社会结构的“第一个人”。而当地人才是那个生活世界的永久人。
那么,研究者的感受最终去了哪儿?

《教授》(The Professor2018)剧照。
两个去向与一个神话
感受,最终大约有两种去向。
第一种只被留存为私人记忆,譬如对于问卷调查来说,研究者使用的大多是封闭式问题(限定了ABCD等选项),根据受访者填写的答案就可以搜集齐全经验材料,一般用不上研究者本人或受访者任一一方在调查现场的情绪、态度,因为它们被视为意外的、无关紧要的插曲;第二种则被当作经验材料,实际上,非封闭式提问的、有观察的实证研究都根植于感受,而这包括五官感觉并接收到的经验材料,比方说,看到的颜色、空间、关系,听到的寒暄、吵闹,还有受访者的情绪、境况等。
前一种去向常见于定量研究。也因此,量化研究经常遭遇责难,被质疑把人的行为、态度简约成统计数字了,而人在其中只是一个可替换的样本罢了,主体性被磨灭了,剩下的只是非情感的、非历史的躯壳。后一种去向常见于质性研究,或融合了质性、量化两种取向的研究。因此之故,人们普遍认为,质性研究尤其是田野调查更尊重人的意义,也更可能理解人的行为和情感之复杂性。2003年,晚年费孝通发表了《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3期,收入《费孝通全集》第17卷)一文,指出田野调查是一种平等的学术实践,研究者、被研究者有条件实现心态感通,其基本方法叫作“将心比心”。同样致力于研究范式本土化的另一位社会学家叶启政自上世纪以来,也不遗余力地揭露统计迷思。(可参考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实证的迷思》,2018年2月)在两位老先生的基础上,若我们了解均值、回归等基础统计的局限,多半会同意质性研究尤其是田野调查确实善于处理感受,故而具备感受性。
到此,我们十分有必要做个区分,把“社会学研究”的感受性与“社会学家”的感受性区别开来,如果缺少这一步,可能不会清楚感受性最后究竟是在什么地方出问题的。
在现代知识界,人类经由实地调查积累了知识,而实地调查实际上也塑造了一个关于研究者角色的神话。这个神话认为,研究者是一个中立的、崇高的材料搜集机器,没有利益、没有性别、没有历史、没有情绪。20世纪30年代,师从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的人类学学生施默勒(Henrietta Schmerler)在田野调查中被当地的白山阿帕契部落奸杀,随后却被当作愚蠢的研究者来取笑。(参考自公号《结绳志》2022年6月17日文章《田野、社会、性暴力》)在将来,这必然会成为反思这个神话的一个案例。施默勒以研究者的身份进入了当地社会,终于被接纳了,但不是被当作研究者,而是一个有性别的、年轻的人。所谓学者、人类学者或推而广之“社会学者”,说到底同样是一个来自生活世界,并按照生活世界规则生存的“人”。
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对此倒有一段比较通透的看法。他是这样说的:
“如果社会学家致力于生产真理,那么他这样做并不是无视生产真理过程中的利益,而正是因为他有利益牵涉其中——这与通常关于‘中立’的愚蠢论述完全相反。就像在其他地方一样,这里的利益包括成为第一个发现者并占有所有相关权利的愿望,也可能包括对某些形式的支配及科学界内捍卫这种支配的人表达道德愤慨或反抗。总之,没有无瑕疵的观念。如果我们非要以发现者的意图并不十分纯粹为由,谴责这个谴责那个,就不会有多少科学真理了。”(引自上海文艺出版社·拜德雅《社会学的问题》,曹金羽译,2022年2月)
社会学研究对感受性的强调、描述,其实只是生产知识的一种技艺。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质性和量化两种方法论长期博弈的结果,它被持续要求提高发现问题和叙述问题的能力,以在知识体系中占据一席之地。当研究者离开理论世界,回到生活世界,其本人的感受将遵循另一套逻辑。在这个意义上,一个社会学家是采用量化还是质性研究取向,与其感受能力并无什么本质关系。换言之,计量、统计研究者在日常生活中使用费孝通的“将心比心”方法,也照样突出了对人的感受性的尊重。
倒有一点,布迪厄似乎误会了“中立”——假如他用的是马克斯·韦伯的概念。韦伯对价值中立的阐释奠定了现代社会科学的基础,但这普遍被理解成韦伯驳斥一切价值判断。他其实只将价值中立限定于操作过程,即材料搜集、筛选和分析等环节,至于研究什么问题(判断什么问题重要)、以什么形式发表研究结果(判断什么形式是有效的)并不受约制。也就是说,纵然承认研究有个人利益牵涉其中,也不是像布迪厄说的,“与通常关于‘中立’的愚蠢论述完全相反”。价值中立的原则不会承认那个有关“研究者”角色的神话。当人们担忧学者不能与人共情时,这感受性指的不是技艺,而是理解他人处境的能力和意愿。
问题是,研究者的情感及其表达经常被认为是不高级的,是被摒弃的。
高级的,被摒弃的
社会学从诞生起就没有停止过模仿自然科学,在实现学科建制的过程中,它形成了搜集材料的体系,一些比较连贯的、可证伪或证实的假说。这是社会学发展的重要基础。遗憾的是,社会学家也拿来了几个与此南辕北辙的,独属于自然科学(有的生物学也不具备)的科学观念,其之一是追求因果法则的唯一性,并认为那是理性的、高级的,从而否定人的感受性。

《穿越西方社会理论的省思》,叶启政著,浙江大学出版社·启真馆,2019年6月。
叶启政写《拆解“结构-能力”的理论迷思》(参考自浙江大学出版社·启真馆《穿越西方社会理论的省思》,2019年6月),说了这么一句比较激进的话:“对人类来说,自古以来,生命的意义,毋宁是与欣赏艺术一样,原本就无法单纯地依靠理性思想挤压出来,而是必须抖动人们的感觉之弦,才可能剔透出来,思想顶多只是被用来整理感觉而已。”他认为感受是理解人类社会的基本方法,而理性只是辅助工具,被用来判断和甄别感受。接着,他说,“经过物质化之科学理性的洗礼,人类早已被导引陷入强调‘客观’之一元判断的泥沼当中,让人类本有的洞识与感受能力遭到严重的压抑”。
过去,人们经常以为,社会学模仿自然科学需要反思的地方是,使用了计量、实验,或追求“假设-演绎”法则,其实可能不然。这是因为这些方法确实影响甚至改进了社会调查。“追求因果法则的唯一性”反倒或多或少被忽视了。
倒不是说缺乏同类反思。最经典的是韦伯,他在早期论集《罗雪尔与克尼斯》就开始了反思。罗雪尔(Wilhelm Roscher)放弃了在纷繁复杂事件中发现法则的古典经济学做法,韦伯认为他的反思还不够,因为他认为发现因果关系即可发现法则,而韦伯对因果关系尤其是单一因果关系都是怀疑的。
![《罗雪尔与克尼斯》,[德]马克斯·韦伯著,李荣山译,李康校,上海人民出版社·世纪文景,2020年3月。](https://x0.ifengimg.com/ucms/2022_27/F39FA3762A6E0A4333F55672E6E9E2B5D818D8B6_size59_w904_h454.png)
《罗雪尔与克尼斯》,[德]马克斯·韦伯著,李荣山译,李康校,上海人民出版社·世纪文景,2020年3月。
说到底,“追求因果法则的唯一性”是一种知识傲慢的体现。持这个观念的研究者,试图把发现、推理强加给别人,使之成为客观表征。
在此意义上,叶启政先生把“追求因果法则的唯一性”描述为社会统计研究的病症,是有失公允的。不少社会统计研究的数据、模型和结论,能通过部分重复来证实或证伪,学术刊物推动的“开源性研究”(提供原始数据下载)也能发挥作用。可能,这一知识傲慢与研究方法取向没多少关联性,它是每个无差别的傲慢者的武器。并且,知识傲慢也不只是体现于解释问题,还包括认为什么问题是重要的等环节。比如,研究者认为A问题是唯一的、根本性问题,否定其他人提出的其他问题。在理性主义、实证主义的双重加持之下,一切感受中关于情绪的、情感的部分都被排斥了。
感受其他人的情绪、情感,在某种意义上也是社会学家的研究范畴。按照涂尔干(Émile Durkheim)对社会事实的定义,一个人的情感不是社会事实,当一个群体或某种相同身份的人群普遍产生了某种情感,并能对个人形成影响,那么就是社会事实。再按照他的第一、第二准则,社会事实当被当作“物”来考察,社会事实能够而且只能用其他社会事实加以解释,而不是依靠推测或臆断。
然而,不只是研究者可能怀疑感受的意义——能写进研究论文的“感受”才被视为有用的——连其他人也可能怀疑感受相对于学者专家的理性是否低人几等。如果你为此困扰,米尔斯(C. Wright Mills)对人的感受性的肯定,可能会提供一些知识上的帮助。他在《社会学的想象力》中主张“从记者到学者,从艺术家到公众,从科学家到编辑”,把个人感受到的困扰想象为公共议题,在历史中看见人与社会交织互动的细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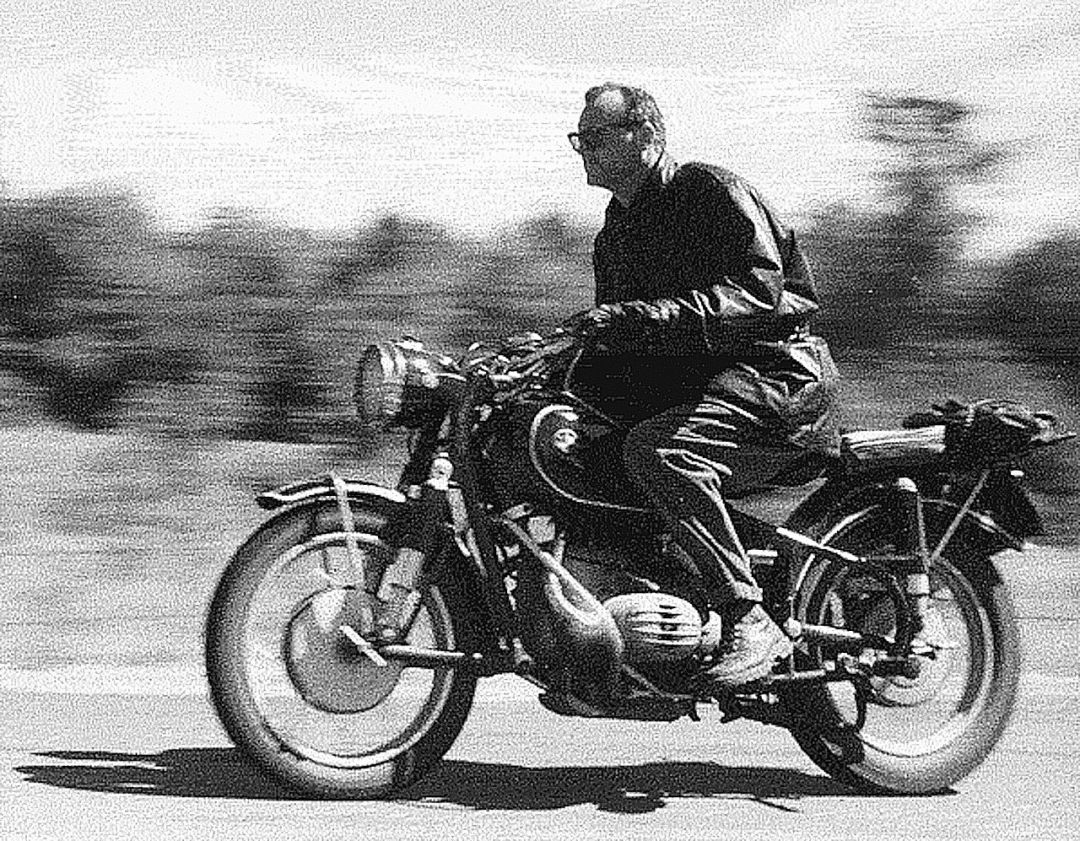
米尔斯(C. Wright Mills),生于1916年8月28日,卒于1962年3月20日。
从知识的角度看,感受是一切知识、道德最初的那个动作,有感受,才有材料,接着才有研究、理解。也可以说,感受是自发的动作,而理性、科学、社会学都是需要发展和训练才能拥有的文明,悖论的是,它们反而借此束缚了人的基本感受能力。有意思的是,人类在设计伦理道德时,偏偏是远离“文明”的。譬如,先哲孟子讲:“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良能良知都是被赋予的、不学而得的品质。欧洲人沙夫茨伯里(Anthony Ashley Cooper, 3rd Earl of Shaftesbury)在1711年的《论人、风俗、舆论和时代的特征》(中译本见上海三联书店,2018年11月)中也认为,是非之心就像自然情感本身一样自然,任何观点都不能够立即或直接地摒弃或破坏它。
潘光旦在《中国人文思想的骨干》(收录在江苏人民出版社2018年7月《潘光旦:守住灵魂的底线》等)一文中对人是这样定义的:“人文思想者心目中的人是一个整个的人,囫囵的人。他认为只是一个专家、一个公民、一个社会分子……不能算人”。当我们提问人的感受性时,研究者身份和他/她作为教师、朋友和网民等身份是需要并在一起的,作为技艺的“感受”,不能描述整个人的感受性。故而,要求人的感受性,是在要求一个人无处不在的感受能力和意愿,理解他人的处境。

1956年12月,潘光旦(中)在湖北四川等地进行社会调查。照片出自《1956,潘光旦调查行脚》(张祖道;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2008年8月)。
然而,社会学将其本身作为反思对象是需要极大勇气的。它已经被理性、科学注解。艾德加·莫兰(Edgar Morin)在《社会学思考》中感叹,“主体已经作为可耻的残余物遭到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摒弃”(转引自《范式与经验之间》,《公共行政评论》2011年4期),陈映芳接着莫兰的话,发觉“似乎一旦让有关‘研究者主体’的问题成为一个公开的讨论议题,那就可能导致社会学原本脆弱的科学性遭受重创”。社会学是一门有着、并受益于科学特征的学科,如果研究者吸纳的是“因果法则的唯一性”这等不可实现的法则,并宣称其是理性的、科学的,否定其他人的感受性,那么他/她本人已经失去了感受能力。






